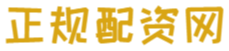2024年12月2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以下简称《科普法》)。相比22年前旧版的《科普法》,此次修订版本在内容上有了很大的变动。针对这些变化,这里选择其中三点,做一些简要的解读和讨论。
其一,《科普法》的总则,是对我国科普整体方向和目标的规定。在这部分,新修订《科普法》的第四条明确提出,“科普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创新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国家把科普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加强科普工作总体布局、统筹部署,推动科普与科技创新紧密协同,充分发挥科普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中的作用。”这种新增的表述,以极高的站位明确了科普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明确了科普与科技创新的关系——同等重要,也强调了科普与科技创新要保持紧密联系并且相互协同。
从原则上讲,科普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这一说法被写进科普法,显然为科普工作之重要性的提升给出了法律上最重要的支撑,但从现实来看,要将此立场落实,还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毕竟长久以来,科技创新的地位在众多研究人员和管理者的心目中还是远比科普更重要的,这样的观念自然会影响到众多科研人员和科普工作者对其工作的认同和考核,会影响到对科普之支持和对科技创新之支持上的不对等。不过,一旦有了这种法律规定的保证,显然对于改变传统观念和政策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从而为新时代推进科普工作带来全新的局面。
其二,长久以来,由于多种因素,科普领域对于科普活动的重视要远远大于对于学术性科普研究的重视。由于缺乏科普专业人才的培养,科普工作者的专业化进程和学术性科普研究难以有所作为。这种现实的存在,与某种过于追求短期见效的功利心态和学科与人才培养体制发展的阶段性密切相关。实际上,像其他领域一样,没有坚实的学术研究来支撑,必然会导致在实际科普活动中存在着种种不理想的情况。因为要进行作为实际科普工作之基础和支撑的科普学术研究,其前提条件,就是要有相关的学科和专业设置,并培养出专业的,而非仅仅是从其他专业转行从事科普工作的专业人才。
在这次新修订的《科普法》中,新增加了“科普人员”的专章,对科普人才的培养和科普人员激励机制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其中提出国家要“支持有条件的高等学校、职业学校设置和完善科普相关学科和专业,培养科普专业人才。”从更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对于弥补以往在科普人才培养的学科和专业设置方面的缺陷,对于解决专业科普人才和学术性科普研究成果积累之欠缺,真正将科普理解为一种需要学术研究支撑和指导的专业性工作,能够在高等学校、职业学校设置科普专业(当然也可以是更为宽泛的科学传播专业),这样的规定显然为未来的改变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同样,像这种涉及教育和研究体制的改变,也许会需要一个过程,但这样的法律规定为我们展示了未来的发展前景。
其三,在过去的《科普法》中,虽然规定了科普的范围包括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但这毕竟还是对科普内容之比较笼统的规定。在这次的修订中,新《科普法》第六条明确地提出了科普工作应遵守科技伦理的要求,并在第二十条中,提到高等学校应开展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教育。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全新的重要变化。
近些年来,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面对随着科技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科技伦理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对科研工作的管理要求中,对于科技伦理的要求也愈发明确,但就对科研伦理的认识和遵守而言,距理想的标准还是有一定差距。新修订的《科普法》,从科普的角度对科技伦理的强调,以及对高校要开展科技伦理教育的要求,显然是与当下科学发展的现实需要一致的,并将科技伦理的教育和普及推广到公众中,为科技伦理的传播和普及开拓了更大的空间。以往,学界甚至曾讨论过与科普关系更为密切的“科普伦理”问题。这次修订虽然没有直接提到“科普伦理”,但它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是包括在科技伦理中的一个子项。应该说,从科普的角度强调科技伦理,与科普的总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也即在新《科普法》中的第三条所规定的:科普“应当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培育和弘扬创新文化,推动形成崇尚科学、追求创新的风尚,服务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科技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撰文:刘兵(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证券杠杆,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主任)